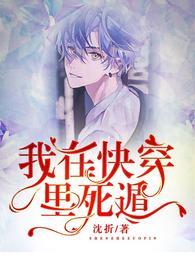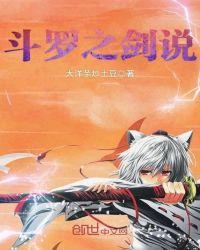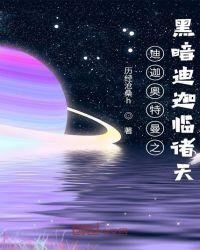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红楼之黛玉长嫂 > 200第 200 章(第1页)
200第 200 章(第1页)
春去秋来,岁月如流。明慧书院的梅树年年花开不败,仿佛时光在此处也放轻了脚步。紫绡已不再登台讲学,却每日端坐于堂前廊下,手持一卷残稿,细细校勘。那便是《未竟篇》的修复本??三年前,她召集天下精通古文、律法、医农之学的女子百余人,在霍七娘亲率卫队护持下,闭门三月,逐字比对、补遗、注解,终使黛玉遗志重见天日。如今此书已非秘藏,而是列为新政诸道官学必读之典,称“新法双璧”,与《女子权益法典》并列朝堂。
然而真正的斗争,从未因一场胜利而终结。
这日清晨,长安城外传来急报:江南漕运断流,数百艘粮船滞留镇江,皆因沿岸豪族私设关卡,拒缴新税,且煽动水工罢工,声称“宁饿死不纳妇人之赋”。更令人震惊的是,有流言自洛阳传出,说沈素衣暗中勾结西域商贾,借“民生改革”之名行敛财之实,所设医馆实为采生折割之所,专取童男童女心血炼药以延己寿。荒诞不经,却已在民间广为流传,数地百姓焚香祭祖驱邪,甚至有母亲将女儿藏入地窖,惧其被“辅政四卿”掳走。
紫绡听闻此事,手中茶盏落地碎裂。
“他们开始攻击人心了。”她喃喃道,“不再是律法之争,而是要让百姓恐惧我们。”
柳青鸾拄杖而来,面色凝重:“不止如此。昨夜我收到密信,河北某县令竟下令拆毁女子学堂,理由是‘屋梁刻有反诗’。经查,不过是学生习字时抄录《未竟篇》中一句‘土地归耕者所有’,便被指为鼓动民变。已有三人被捕入狱,其中一名十六岁女童被刑讯逼供,咬舌自尽未遂。”
紫绡闭目良久,指尖抚过案上《未竟篇》扉页上的墨迹??那是黛玉临终前最后一笔写下的批注:“变革之难,不在破旧,而在立信。若民不信官,官不信民,则法令如纸,烽火可燎原。”
“我们必须亲自走一趟。”她说。
三日后,一辆朴素马车驶出长安,无仪仗,无旌旗,只有一面小小的梅花旗斜插车辕。车上坐着紫绡与柳青鸾,另有两名年轻女史随行记录。她们的目标是河北深州,那个拆毁学堂、囚禁学子的地方。
路途艰险。沿途村镇张贴揭帖,绘着四位“辅政卿”披发跣足、手持利刃屠杀宗祠祖先的画像,旁书血红大字:“妖女乱国,天怒人怨!”更有孩童唱起童谣:“四娘执政颠阴阳,爹娘不敢管婆娘;学堂教女不织布,将来谁来养公婆?”
紫绡听着窗外歌声,沉默不语。直到夜宿驿站,她才低声问柳青鸾:“你说,林先生当年可曾想过,她的名字有一天会被编进童谣里,当作吓唬孩子的鬼魅?”
柳青鸾苦笑:“她若知道今日仍有孩子能读书识字,哪怕是以恶名传世,也会笑出声来。”
抵达深州那日,天降细雨。
县城门口,一群乡绅列队相迎,个个面带倨傲。为首者乃本地望族赵氏家主赵元礼,头戴儒巾,手持拂尘,自称“承先圣遗风,守礼教纲常”。他当众拱手道:“听闻紫夫人亲临,特备薄酒接风。只是近日县中学堂闹事,伤及尊长,恐有污视听,不便开放参览。”
紫绡下车,撑伞立于雨中,目光平静:“我是来看人的,不是来看房子的。请带我去见那些被拘的学生。”
赵元礼脸色微变:“此等逆女,岂堪面见贵人?待审明罪状,自然押送京师法办。”
“不必了。”紫绡声音不大,却穿透雨幕,“我现在就要见她们。否则,我将以‘阻碍新政巡查’之罪,当场革去你一切功名职衔,并奏请朝廷派监察御史彻查此案。”
人群哗然。
赵元礼怒极反笑:“你不过一介女流,虽蒙圣恩忝居高位,怎敢在地方擅行威福?这里不是长安,轮不到你们这些……”
话未说完,一道寒光骤然掠过。
霍七娘不知何时现身,一身黑袍湿透,肩披斗篷,手中长剑已然出鞘三寸,剑锋直指赵元礼咽喉。
“你说完了吗?”她冷冷道,“我可以现在就砍下你的头,也可以等你跪着听完圣旨再砍。选一个。”
赵元礼浑身颤抖,终是退后一步,挥手命人开监。
牢房阴暗潮湿,霉味扑鼻。三名少女蜷缩在草堆上,双手戴枷,嘴唇干裂。最年幼者不过十三,右臂缠着渗血布条,见有人进来,本能地往后缩。
紫绡蹲下身,轻轻解开她的枷锁。
“疼吗?”她问。
女孩摇头,眼泪却滚了下来:“先生……我只是念了一句书……他们说我要造反……可我只是想当个教书先生……”
紫绡将她拥入怀中,喉头哽咽。
“你想当教书先生?”她轻声说,“那你一定会成为最好的先生。因为你知道痛,所以懂得温柔;因为你被人关起来过,所以永远不会把别人关起来。”
当晚,紫绡在县衙大堂召开民议会,邀请士绅、里正、农夫、寡妇、塾师共六十人参会。她并未宣读律法,也未斥责官员,而是请三位受害女童依次讲述经历。当最小的女孩含泪说出“我想教妹妹认字,可爹说女孩子读书没用,还不如早点嫁人换彩礼”时,满堂寂静。
一位老农忽然站起,颤声道:“我家闺女去年上了识字班,今年帮村里记账,省了两贯钱。我还骂她不安分……今天听了这话,我才晓得,是我错了。”
又有一名寡妇哭诉:“我男人死后,族里夺田夺屋,说我不能继产。幸亏《法典》下来,我才保住三亩薄地。若不是这书,我早投井了!如今你们反倒要毁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