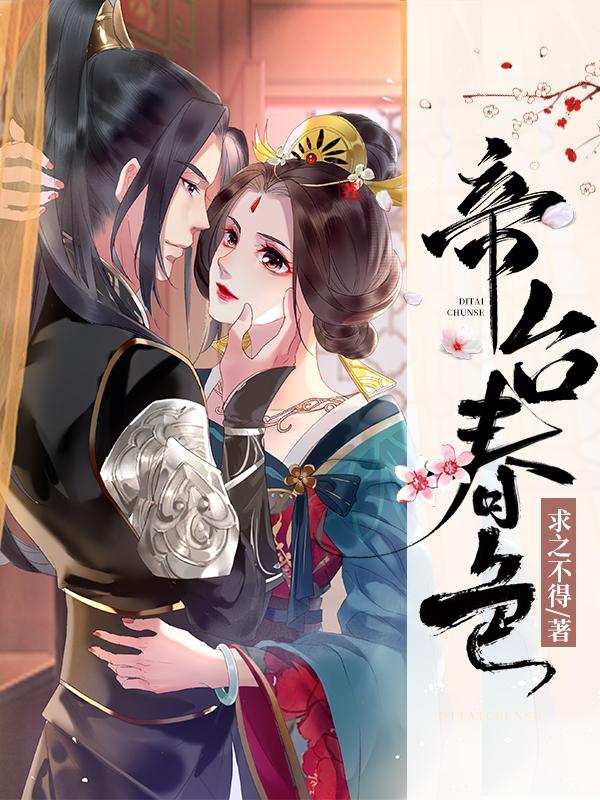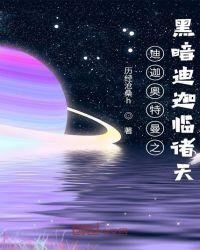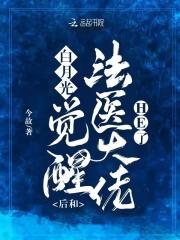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最美好的年华遇见最美的你 > 甄亦凡和林依婷的故事font colorred番外font(第1页)
甄亦凡和林依婷的故事font colorred番外font(第1页)
记忆中的那泓微笑
每个人的内心里都有一块柔软的地方,那里收藏着你我无意间留下的,一些小小的善良和温暖。
——题记
2005年夏日的某一天晚上,书房里柔和的灯光下,林依婷打开那份还散发着油墨清香的《都市晚报》,那是白天中专室友方陈莯鸿特快专递寄来的,上面刊有甄逸凡的散文《记忆中的那泓微笑》。
“人生中,总会有些记忆,谈不上刻骨铭心,却总令人难以忘怀,就如我们偶尔遇到的风景,虽是淡淡的,却自有她的一份美丽。
我不知道婷的微笑是否属于这一类,但我亦明白,或许今后的岁月里,我是无法忘却那泓淡淡的微笑的。
那时,刚从湘西北一个偏远的山村考上省城一所重点中专,初到繁华都市,我有一种茫然感。那段日子,也别提有多消沉多黯淡了。我喜欢写作,却总是将自己锁在图书室和日记本中。我想,要不是那泓微笑,或许我一直无法走出那种黯然的生活。学校文学社复社时在全校学生中竞选社长,我很想借此机会塑造同学们眼中一个全新的我,却又极其害怕失败。正犹豫间,一个声音飘了过来:“你行的,我相信!”抬起头,正看到婷那微微的笑靥,高挑的身材,一身火红的风衣,在这寒冷的冬季,那微笑恰似一朵含苞欲放的蓓蕾。蓦然间,我的心里亮堂了,那粲然的笑容所蕴含的一切,不正是我所苦苦寻觅的么。笑靥如花,犹如一道美丽的风景,在这中间我发现了一个全新的我。尽管那次竞选社长未能如愿,但最终依靠自己扎实的写作功底和对文学的痴迷热爱担任了社刊的主编。生活,为我打开了另外一扇窗口。
打那以后,我们的交往也似乎多了些,常常有意无意间同行,有意无意间相遇。也常常有一些默契的配合,打扫卫生她拖地扫地,我会一张张搬开桌椅;我擦窗户玻璃,她会双手撑稳桌椅,一次次接过我手里的抹布洗干净了再回递给我;早上跑步会操常常会彼此不期而遇。但说来也许令人难以相信,我们的交往,一直局限于彼此交换一个会心的微笑,一道心领神会的眼神。那是个心灵敏感多疑的时代,我们都小心翼翼地守护着这份情感,生怕它深化,也怕它淡薄。但我不得不承认,她的微笑,每次都能给我力量,给我信心。每天早晨,只要看到她的微笑,接到她的眼神,这一天,我就充满了希望,只要一见到她的背影,或听到她的声音,我就有一种充实的感觉。
也许是她无声地鼓励,使我在四年中专生活中取得了一些进步和成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的初恋的感觉。尽管也曾为她记过日记,写过诗歌,但我们却一直没有深入地交谈过,也许是她那淡淡的忧郁和娴静所体现出的一种古典、淡雅的气质使人不忍破坏这份完美吧。我们就一直这样保持着这份淡淡的交往,淡淡的友情,还有一次次有意无意间默契地配合。我不知道,这是一种遗憾还是一种幸运。四年中专生活就在她淡淡的微笑中慢慢滑过了。毕业之际,我有一种预感,也许自此一别,再难相聚,怀着一份莫名的惆怅,我写了那首《也许》‘也许往日的琐事会淡化也许邂逅的细节会失真也许梦幻会褪去色彩也许日子会老去而这份情,却日益年青是否梦浓时分正是梦醒时刻是否所有邂逅总如雨后彩虹如果前生已定而今世难求那么我信佛,坦然面对你的离去你走后的每个日子我会默默许愿用今生,祈求我们下世的情缘。’
那令人心碎的低低一声‘珍重’之后,我们再没有见面,但那泓微笑却一直停留在我心灵深处,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不断进取。”
一字不落的看完《记忆中的那泓微笑》后,林依婷翻开了抽屉,从底层的日记本中拿出那张照片。一片山林中,一个少年身背猎枪,面对冉冉升起的朝阳,吹响牛角号角,英俊朴实犹如大山之子。照片的背面,是甄逸凡十年前毕业时的留言,摘抄的是大诗人徐志摩的那首《偶然》“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暗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互时互放的光亮!”
放下手中的报纸和照片,林依婷痴痴地望向窗外,远处的星空,几颗星星眨着眼睛,半轮圆月斜挂在天边。那一幕幕往事,就如发生在昨天一般。
1991年9月1日下午3:30,骄阳如火。16岁的甄逸凡走出省城火车站,一抬眼就看到了学校在车站广场边上拉的横幅:“劳动人事学校热烈欢迎各位新同学来校学习。”拉横幅的树荫下摆着几张桌子,几位老师正在接待一些新生和家长,周围一群十六七岁的少男少女,穿着校服,或叽叽喳喳或主动上前询问经过的学生和家长。甄逸凡独自扛着沉重的大皮箱,头顶烈日,还没走到广场中间,就有一男一女两位同学迎了上来,“是省劳动人事学校的吗?”男生看他点了点头就一手接过了笨重的皮箱,女生则尾随着要接过他的背包。“嗯”甄逸凡轻轻应了声,手里放了箱子却不愿放下背上的包,一个大小伙子,怎么好意思麻烦一个女孩子背包呢,尽管还是位还不知名的“师姐”。甄逸凡来到那排桌子旁拿出录取通知书简单地登记了,就坐在一旁的长椅上等着校车。这一排长椅上已坐了不少学生和家长,都是等校车的。没多久,校车来了,大家一踊而上。
甄逸凡,这个湘西北贫困山区的孩子,开始了他在都市校园四年的中专生活。
其实一下火车,这个乡下长大的孩子就被都市里的繁华所震惊,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满大街鸣着喇叭的车辆和川流不息的人群。给他带来更大震撼的是身边的同学,甄逸凡这次以全县第二名的好成绩考上这所全省重点中专,而且有几门课还是满分。开学了,他才明白当时老乡接他下校车时的一句话“这里很难考的,有湖南‘小清华’之誉”,他的成绩在全班49名同学中仅列中下游而已。当晚上在宿舍睡到半夜,听到下铺那位来自常德的李同学睡梦中还在背着英语单词时,他真正震撼了。
最让甄逸凡害怕的是每天早上的课前15分钟,遇到语文或英语,老师往往要求课前15分钟朗诵课文。语文还好点,虽说他的普通话不是很标准,但好歹能结结巴巴地读完整,再说也不是每次都点到他的名。英语就让他有些为难了,他没进过县一中,就读的乡中学,两位曾教过他的英语老师都是学校请的代课教师,也只是个高中毕业生而已。那时在乡下,大多只注重考试考了多少分,没有哪个学校将英语的口语和听力当成一回事,所以他三年来所学的英语基本上都是“哑语”,“我是中国人,不学外国文”是那时班上大多数同学的口头禅,他和同学们经常将英语标上汉字“注音”,比如“恩格里西English”“古的阿伏龙Goodafternoon”诸如此类。每每英语课上点到他的名时,他都只是嗑嗑巴巴地读几个单词就一脸通红地不知所措了,虽说没有同学笑他,可他的自尊心一下子就碎了一地。偏偏这位年轻的英语老师对学生很负责,经常点他的名,说是鼓励他多读,且时不时课后还把他叫到办公室开小灶教他,鼓励他,可要一下子赶上这些在城市就读的孩子们的口语,他真的找不到办法。
作为一个初入都市的青春期孩子,他有自卑和不快,但更多的是惊喜和快乐。这个繁华的都市,时不时给他这个从小生活在乡村里的孩子一些惊诧,比如宽阔的马路上川流不息的小汽车,高楼大厦里面繁华的商场。一到星期天他经常和室友吃过早饭就步行10多里到城市中心去,体验那份城市的喧哗。
他最感兴趣的还是学校的图书室和阅览室。图书室虽说在省城的学校里排不上号,但对于他这个山村孩子来说,无疑是个宝藏。他常常借了书半夜里趴在床上打着手电偷看,无论是金庸、梁羽生、古龙的武侠小说还是琼瑶的言情小说,还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他都饥不择食。阅览室里也常常有他的身影,《知识博览》《中国校园文学》《读者》等杂志是他的最爱。以至于进校不到三个月,他忽然发现自己的眼睛有些近视了,不得不配了副300度的眼镜。最让他惊叹和喜欢的是袁家岭新华书店,那是省城最大的书店,10多层,每层面积都是那么大,一眼望去满满得都是书,许许多多他初中时听说过或未听说过的书,都分门别类地码在书架上。星期天,他常常和室友进城后就各奔东西,他绝大多数时间都是耗在书店那层卖文学书的地方。没有钱买书,他就一蹲一整天,饿了,在外面来碗米粉或买个面包充饥,书店里的书尽管看,不像家乡的书店要收钱,又有空调,舒适爽快,这日子对于他,就如家乡那首山歌里唱的“人似活神仙”。
年轻的心总是充满着好奇,甄逸凡与他的同桌,这个名叫刘雨轩的星城本地女孩,两人的出身、生长环境大相迥异。一个生长在深山老林,自小穿着土布衣服,与广阔的山水自然打交道,常常上树掏鸟窝,下河摸鱼鳖,就是在家里被老爷爷逼着看书,自小看的也就是那几本《唐诗宋词元曲》《四书五经》以及一些《封神演义》等历史演义。而一个是生活在钢铁混凝土筑成的大城市,自小就被《格林童话》《安徒生童话》中的公主和王子生活与《大力水手》《聪明一休》等动画片包围着长大的。彼此对对方的生活充满着新奇和向往,尤其是这位十五岁的女孩,总想到山里的生活特别有味,常常围着他问东问西,叽叽喳喳个不停。
周六中午放学后,刘雨轩按惯例回家去。“跟我回家里恰饭替”,她邀同桌甄逸凡。“好啊”,这一个多月来,食堂的伙食也确实让他不习惯,他们宿舍也先后几次到外面的餐馆打“牙祭”。难得吃一餐家常菜,想起家里外婆炒的菜,他就想得差点流口水。一路乘车到五一路口,下了公交车,他也不知道这位本地女孩家住哪里。一路走着到了省政府大院门口,看着手端钢枪,威风凛凛的警卫,他有点不敢向前挪步,怎么也没想到同桌的家在省政府大院内。到了门口他竟然低头盯着地面临时想退缩,倒是同桌大大方方地一把拉起他的右手,迎着警卫的目光牵着他自自然然地走进大门。同桌家的房子不大,却很整洁,看来她的爸妈或许在省政府工作,也许还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官吧,不然也不会在这个院子内分到一套房子了。同桌的爸妈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没问,也不敢问。要知道当初在山里一年到头连个乡干部都不容易见到,何况这威严的省政府大院和这院内的大干部呢。同桌的老爸倒是很和蔼,也很热情,让两个孩子在客厅里聊天、看电视,自己在厨房里忙上忙下。半个多小时后,厨房里就飘出来了阵阵香味。支起一张餐桌,就开餐了。尽管刘雨轩和她爸爸很热情,不时给他这个有点腼腆的孩子夹菜,可他毕竟还是很拘束,有些放不开。饭菜确实很香,按说他这个正在长身体的半大小伙子,放在家中可以吃上大半碗腊肉加上一小碗苞谷烧,再来两钵饭。可在这个家里,他只能学着这些城里人一样,慢慢吃,慢慢嚼,很香的饭菜他都没吃出多少味来。吃完晚饭,同桌跟她爸爸打过招呼,送他出来,到大院门口时还没有停步。或许是担心他人生地不熟吧,刘雨轩没有回家,而是一直陪着他坐公交车返回到学校。自然,女生宿舍也有许多人,班上49名同学,来自三湘四水各地市县,除了寒暑假,平时基本上不可能回家,经常能回回家的也就星城本地和湘潭、株洲附近几个县市的同学而已。这些城市,离星城不远,而且每天都有几趟班车,不像甄逸凡他们,从省城回家,要先坐火车,再坐汽车,有的人从乡里到村里不通公路还要走路回家,一个来回差不多要两三天。那时也没有“黄金周”和双休,星期六还要上半天的课,周末一天半的假期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是根本不可能回一趟家的。
甄逸凡很喜欢语文课,虽说普通话不太标准,朗诵课文时结结巴巴乡土音很重,可他毕竟自小在爷爷的熏陶下古诗文的功夫底子还是很不错的,而且自初二起就开始跟着爷爷学写一些古体诗词。因此中专语文课中增加的很多古诗文很对他的胃口,他的作文也还不错。班上第一堂作文课,他的《家乡的木子树》就被语文老师当作范文在班上朗诵了一遍,这个来自山区的孩子,也用自己的方式让大家朝他投来了吃惊而佩服的眼光。尤其是他发表在校团委内刊上的那首仿古律诗《送别》“山重水默寂无声,挚友孤蓬万里征。空有余力时难挽,日落乌啼月催人。马知灵性不肯前,泪溢掩面狠扬鞭。山回路转人不见,但闻长空孤雁咽。”短短八句,对仗工整,意境深远,颇有古风之韵。很难相信出自一个刚刚初中毕业的学生之手。从诗句中随手拈来的意境也可看出甄逸凡受古体诗词的影响颇深,有点“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来也会呤”的味道。
从小生活在都市的刘雨轩很喜欢听甄逸凡讲一些乡村生活的趣事,也常听他讲《封神演义》《薛刚反唐》等一些神话和历史演义。这一切,在这个都市女孩眼中都是那么的神奇。有时兴趣来了,他也会给这个同桌女孩讲一些土家哭嫁、老人去世时的习俗,偶尔也会唱一点《二十四孝》之类的经文,或者花灯戏歌词。当然,这个都市女孩子最感兴趣的还是那些乡村孩童生活,比如上山打猎赶野猪、赶岩羊,和小伙伴们上树掏鸟窝,冬天雪地里支起筛子诱捕小鸟,半夜起来打着手电筒或者竹火把在田间地头夹泥鳅、捉黄鳝等甄逸凡和小伙伴们淘气的童年。有时候听到有味处会忍不住咯咯大笑起来,往往引起班上其他埋头看书的同学向他们投来诧异的眼光。有一次听他讲到土家族妹子结婚哭嫁时,前桌班上那个年龄最小的娇娇女蒋盈盈扭过头来插了一句:“现在新娘子出嫁还有花轿坐吗?”他故作停顿,装作思考了半天才讲“你生迟了,我爹娘结婚
那时是坐花轿的,还有土家滴水床,现在新娘子自己走的。”弄得小丫头一阵失望。
有时放学吃完晚饭后,这个大方的都市女孩也会邀请这个腼腆的乡下男孩去学校后面的山上走走。学校在郊区,农舍、农田、鱼塘还蛮多的,也有小山丘,学生们平时晚饭后或周末经常会三五成群去转转溜溜,舒缓一下压力,呼吸一些新鲜的农村空气。走在山间小路上,两人有说有笑的,玩到高兴处,甄逸凡会忘乎所以,就像在家乡的山野中那样,随手扯片树叶含在嘴里吹起曲子,或者随口吼出几句山歌。家乡的山林里,田间地角边,劳作的人们常常会吼上几嗓子,有时是澧水号子“哎喔哎喔呕喔呕喔哩嗬咳呀,(得)!船怕号子(得)马怕鞭(哪),(得)!不怕风浪(得)高又高(啰)。”高亢有力,节奏明快。有时是山歌比如《嘞嘿山歌》“五句歌儿五句对,只准上前不准退。上前不准伤父母,退后不准伤妹妹,天下只有和为贵。”有时也教她一些小调,比如《花大姐》:“姐儿坐在(三个妹子儿三),花果儿坪罗(两个妹子舍),身穿花衣(格呀格子格),花围裙哪(两个妹子啥),上是格,下是格,格子飞,多是扯,你早些来(呀大姐哈)”,也有花灯调《四季花儿开》,“春季花儿开,花开是一呀朵来,一对呀(的个)鸽子儿呀呵飞呀过的山来呀(哈哈啧啧飞呀啧啧啧飞呀啧啧啧)飞过的山来看啦,瞧见我的小乖乖哐(哥儿,喂!妹儿,喂!哎呀,恩哪爱呀恩哪爱呀真恩爱),夏季花儿开……”自然,那些在家乡随处可闻老少爱唱的一些比如《好郎好姐不用媒》《棒棒捶在岩头上》,诸如此类的火辣辣赤裸裸的情歌,他是打死也不敢张口就来的。毕竟,这里是都市里的校园,不是家乡深山老林也不是河岸滩边田间地角,而且,面对的是一个都市女孩,可不是家乡那些胆大包天的野妹子。
年轻人的日子总是过得飞快,转眼间就期中考试了。由于把精力都放在看书和写诗上,甄逸凡成绩下降的很快。当然,有所失必有所得,甄逸凡的一些散文、诗歌也陆续在校内外团委和学生会所办的墙报和内刊上登了出来。私下里,无论是本班还是外班也有一些师长学妹私下里给了他一个“校园诗人”的荣誉,班上也免不了有一些同学因他不太融入圈子的性格戏称他为“湿人”。
“天已黑了,而手上的表才走到6点12分,究竟是表走慢了还是天黑得太快了?室外,狂风大作,树枝乱摇。呼呼风声,飒飒树叶声,不绝于耳,间或几道闪电,劈开黑暗的天空。乌云压顶,天似锅底一般黑,而四周却是曙白色。间或,雨丝从窗外飘进,打在脸上,冰凉冰凉的。临窗外望,闪电时现,一近一远,雷声暗响。俄倾,“哗哗”雨声响起,雷声在天边不时炸响。雷声消失,闪电即现,闪电一隐,“轰隆隆”的雷声又由远至近滚滚而来,如此交相替换,反复不止。
教室里同学们衣衫飘飘。约十分钟后,雷声越来越大,闪电越来越明,六七秒钟便有一道闪电拉开。
此时方觉身上略微有点冷。
7点左右,雷声依旧,闪电依旧,雨小了点,天空渐渐变为深蓝色,当闪电拉开则立即变成了银紫色。
7点10分雷声似战鼓,一波接一波,闪电也一道接一道,好像有人催着天兵天将下凡除妖捉怪一般,紧锣密鼓10分钟左右,雷声停了,闪电歇了,天色明了,而丝丝细雨则变成了倾盆大雨,蔸头浇下,将天地包了个严严实实……”
——以上摘自甄逸凡11月2日观察笔记。
7点半《新闻联播》刚播完,班主任徐老师匆匆从外面赶来给大家宣布了一个不好的消息:“刘雨轩同学因病休学一年……”其他的话,甄逸凡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耳边犹如外面刚刚过去的雷声,轰轰作响,一瞬间,他的心也跌进了窗外的暴雨中……
新调来的同桌也是一个女孩子,姓林,高高的个儿,不胖不瘦,临近一个地区城市人,据说父母在一座国内综合大学教书。她和每个同学打交道,都是一脸的淡然,常常给人一个微笑,很少看见过她像其她女同学那样开怀大笑,浑身上下,透出一份闲静淡雅的气质,有点古书中“小家碧玉”的味道。也确实,除了努力学习外,也没看出她有啥特长或出彩之处。开始两周,两个安静的人几乎没有搭话,各忙各的。甄逸凡又陷进了那些诗词中,时不时沉浸在那些虚无缥缈的想像里,别说自习时间,就连上课有时也没认真听。而同桌这个女孩则真如宿舍里晚上有些人议论的那样,是一个典型的乖乖女,认认真真地听老师讲课,认认真真地记笔记,就是自习时间也认认真真地复习、预习,连一些课外书也很少看。新同桌和他犹如互不搭界的两条平行线,即使偶尔交集,也只是淡淡的两句闲白话。
可能甄逸凡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个姓林叫依婷的同桌女孩,这个同桌了两周总共还没讲过三句话的女孩,会成为他今后怎么也无法忘怀的那个人,哪怕一生一世!
日子在不咸不淡中过得飞快,这个冬天来得有点早,元旦刚到就飘起了雪花。甄逸凡这两天很高兴,他的《贺卡入梦》,被《星城晚报》副刊采用了。“遥遥的一份祝福淡淡的一份温情飘向你也飘向我载着雪花的温馨雪花飘落化入你的梦中新年的祝福便永不消融。”虽说只有短短几句,在报纸上也只占一个小小的角落,可毕竟是他走进中专后被校外官方报刊采用的第一首诗歌,至少证明他这几个月来的诗歌梦不是“白日梦”。拿到稿费的当天,他邀老乡到校外打了顿“牙祭”。
不过,这段日子对他来讲,比欣喜更多的是苦恼。学校《莽草》文学社团89年因故被停刊,这些年随着校园文学的兴起,周边的大中专院校都办起了文学社刊,学校学生科也准备恢复《莽草》文学社。公开竞选社长的公告早已张贴,本周五是报名的最后一天。甄逸凡爱好文学,也有些功底,自然想去竞选社长,以便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长。可一想到要在阶梯教室面对数百名师生竞选演讲,他就有些心痛气短,不说他的普通话讲得好不好,单就那阵势,他就怯场。要知道,在家乡那所乡镇中学,可是不知演讲是啥个搞法啊。面对这些都市同学,他也知道自己的组织能力、协调能力和演讲口才都是远远比不了的。有时他苦恼的直想骂娘,这个中专,真他妈的变态,藏龙卧虎的太多了,不看别的年级别的班,单单就自己身边的两个同桌,一个父母在省政府上班,一个父母在全国重点综合大学里教书,也不知他们这些大人是怎么想的,竟然将自己的乖乖女放进一个区区中专就读。要知道,就是甄逸凡这个农家子弟,要不是因为家里父母供他们四个兄弟读书负担太重,早就去县一中读高中考大学了,不讲光宗耀祖,至少考个大学出来分配的工作都要好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