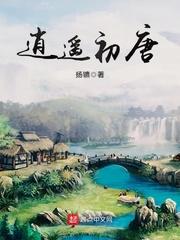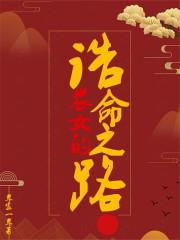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地府皇帝改造指南 > 110120(第2页)
110120(第2页)
虽说三家鼎力,良鸟择木而栖;但大家相持多年,彼此间也算有点默契。要是寻常身份不显的中低层官员,为了荣华富贵投降敌国,那也算是常事;毕竟朝廷于尔本无恩德,也不能指望下面为了五斗米的俸禄鞠躬尽瘁;但司马懿——三公重臣、国之泰斗、领受先帝托孤之重的司马懿,如今居然也悍然跳反,翻脸不认旧情,那带来的刺激乃至恐怖,就实在超出一切预料之外了!
要知道,即使以汉末之纲常扫地,能够坦然无耻地背弃旧主,贪婪无耻到如此地步的,也不过只有吕布吕奉先一人而已。如今司马懿以累世名门之身,行此惊世骇俗之事,冲击力则更比吕布还强上百倍不止——不是,你都不要脸的吗?
以陈群曹真与司马氏相知数十年的交情,实在是很难想象一个不要脸的司马仲达;所以伏地告罪之后,第一反应就是为司马仲达辩驳——当然,他们也不得不辩驳;托孤重臣同气连枝,如果司马仲达是这种失心疯的疯批,那其他重臣当然也就靠不住了——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
司马懿疯没疯不要紧,重点是绝不能把他们这些无辜的局外人给牵扯进去。所以陈群以手撑地,竭力思索片刻,终究还是要开口辩护——他也不能不辩护,哪怕这个辩护很可笑、很站不住脚,也必须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控制住皇帝的情绪,避免事情激化到完全不可理喻的地步——
但很可惜,陈群刚刚匍匐下去,就听到头顶哐当一声巨响,居然是少帝飞起一脚,将面前的书案直接踢飞,书案上的笔墨纸张也一起横飞,浇了身边的小黄门一头一脸;而在杂物翻滚的巨响中,皇帝的怒吼亦随之迸发,震得屋梁簇簇发抖:
“老匹夫,老匹夫!朕早就知道,这些老忘八看似道貌岸然,心里其实在藐视朕躬,藐视皇统,藐视列祖列宗——什么扶持幼主,什么领受遗命;狗屁,狗屁!现在狗尾巴藏不住了吧,啊?!”
说到此处,少帝呼呼喘气,又抓起身边的如意,当啷一声扔向一片狼籍的书案——显然,在收到过好几次被精心炮制过的书信之后,少帝的精神也早就在崩溃的边缘了;更不用说,这一封信毫不留情,居然还悍然向他最痛的地方戳下去——如果说先前信件中的阴阳怪气还只是挑动疑虑,那么这最后一封书信,则无疑是点破了所有的恐惧:
司马懿就是在图谋不轨;司马懿就是看不起他;司马懿看不起他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孝顺先帝——那个害死了少帝亲娘的先帝;推而广之,如果司马懿都因为先帝的缘故而厌恶他、看不起他,那么其他大臣呢,其他被先帝简拔起来,受命“辅佐”他的大臣呢?
少帝不能再想下去了。他只觉头晕目眩,精神恍惚,于是晃晃悠悠,一屁股坐到了御榻上;然后支持不住,又仰面向后栽去,好容易才被身后的小黄门抱住,小心翼翼扶了起来。
按理来说,君主被气得神智不清举止恍惚,重臣们是该立刻抢上前去查看状况的。但底下匍匐的几人都没有动弹的意思;不但没有动弹的意思,甚至还把头埋得更低了。听话听声,大家别的不明白,皇帝口中那种毫无掩饰的怀疑,肯定是一听就能听懂,绝不会有任何怀疑——你骂司马懿就骂司马懿,什么叫“这些老忘八”?这些老忘八中,到底还有哪个带怨种?
既然皇帝已经多疑成这样,那就基本是说什么错什么。就算他们上前扶了一把,恐怕也要被小皇帝怀疑是别有用心,蓄意暗害;既然如此,不如大家一起趴在原地,静悄悄等着君主发完这个疯癫,这才是上上之策。
是的,虽然少帝登基以来,一直尽力维持着威不可测的高深形象,行为举措也总是恰到好处,不堕声名;但下面的重臣人老成精,依旧一眼看透了少帝的本质——无论少帝多么冷淡他那个喜怒无常、情绪不定的父亲,他的内在都与先帝并无区别;依旧是一个容易被外在影响挑动心绪的敏感文青;因为这个微妙的特点,司马仲达的尖刻书信才能一击致命,制造如此立竿见影的杀伤。
当然,司马仲达能够影响的,其余重臣也同样能够影响。重臣们非常清楚,等到发泄完他的无能狂怒之后,年幼的皇帝必然会陷入某种近于无助与恍惚的虚弱之中,这个时候设法游说,才能够一举攻破心防,收获奇效。
所以,有见识的老臣们都在屏息凝神,默默等待,等待着皇帝在狂怒中胡言乱语,大失常态;或者干脆绷不住直接哭出来——司马懿悍然跳反,这是足以动摇整个政权根基的大事,以小皇帝那点孱弱的根基是根本处理不过来的;无论多么怨愤、疑虑、不情愿,在发癫之后,小皇帝都不能不面对残酷的现实,最终无奈妥协。唯独在这一点上,他们有绝对的把握。
……然后,他们就听到了小黄门惊恐地一声大叫;陈群等抬起头来,恰恰看到少帝软绵绵的从榻上滑了下来,一张脸惨白如纸,已经再也没有了血色。
无论洛阳朝廷发生了什么惊天变故,对于困守前线的郭淮来说,都已经没有意义了。他原本以飞马向朝廷寄信,还妄想着洛阳朝廷能够从什么地方挤出兵力强行支撑一下前线的危局。但事态进展数日,他就很快发现了这个妄想的荒谬之处——诸葛亮怎么可能会给你从容求援,巩固防线的机会呢?
总之,在“菜地之战”后的第三日,蜀军即整顿旗鼓,全面进发,向前线一举压了过去。而魏军屡遭动荡,战意已失;即使仰仗着之前修筑的诸多坚固工事,也根本没有了决战的信心,稍一接触立刻崩溃,甚至有士兵临战溃逃,宁愿转身面对督战队的刀剑,也不愿顶在前方白白送死——于是维持数月之久的均势,一朝尽数崩塌,局面急转直下,再也不可收拾。
以战线而计,蜀军发动攻击的第二、三日,魏军设立在褒斜、子午内外的所有防线就已告崩溃;汉中尽数易手;第五日,蜀军击穿魏军沿渭水设置的所有防线,兵锋直指泾水;至第七日,蜀军攻势稍缓,诸葛亮却大张旗鼓,派人招降安定太守——安定郡倒没有直接投降;但态度暧昧狐疑,踌躇不决;居然还派人将招降的使者好好送了回去,还附赠了几筐绢帛,作为回赠诸葛丞相的礼物。
到了这一步,所有人都能眼睁睁看出来,安定郡已经完全靠不住了!
安定郡靠不住,汉中防线又全面崩溃,如今长安以西,恐怕全都是蜀军的天下了!
面对这样惨烈的败局,郭淮也不是没有做过努力;他的战略倒是非常清楚,即抛弃部分已成死局的据点,将兵力收缩到关键堡垒,能够挽回多少就挽回多少。但很可惜,想法固然完美,执行却是天难地难,不说士气拉垮后什么军令的效果都要打个折扣,就说这个军队转移——诸葛亮能眼睁睁的看着你转移兵力么?
过水有水攻,过林有火攻;山道有埋伏,平地有机关;当初为司马仲达准备的套餐,如今一样不落,原模原样的为郭淮照搬了过来,而且照搬的效果,还要大大强于往昔——司马懿时魏军信心还在,关键的地利尚且在手,就算一时中了埋伏,损失也不会太大;但到了现在嘛……诸葛亮规划的战术中,主力部队由他全面控制,负责一个据点一个据点的敲掉魏军的钉子,而其余奇兵则由某两位姓霍及姓卫的军事顾问掌握,负责在侧翼袭扰预备收缩的魏军主力,而那个结果嘛……
交手第十二日,郭淮紧急向长安派遣使者,传递口信;而口信也只有一句话:
“事急矣,宜善谋之!”
——要完犊子了,各位自己看看该怎么办吧!
曹魏建国以来设立了五个都城;理论上讲,长安作为西都,作用是坐镇西陲威慑巴蜀,顺便打通前往西域的通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安排的忍受也都该是当时的俊杰。但可惜的是天下的规矩大家懂的都懂,靠近权力中心的距离越近,也就越容易掌握权力;所以一切有志于往上再进一步的卷王,那是绞尽脑汁都要往洛阳中挤;只有政治斗争中黯然退场,再也没有影响力的尊贵吉祥物。这些吉祥物被外放到长安,那肯定不是雄心勃勃、再创伟业的,长安上下普遍的目标,基本就只有一个:
躺平。
这种躺平的风气非常严重,而且根深蒂固,不可遏制(废话,政斗都失败了还卷什么?),所以历年曹魏用兵,宁愿千里迢迢从洛阳从辽东派人奔赴渭水前线,都绝不愿意惊动长安城里这些暮气沉沉的老宝贝。这也是魏延信誓旦旦,对子午谷奇谋这么有信心的缘故——长安城中的老宝贝们躺了十几年,如今哪里还有什么战意?只要兵临城下,不就能一举克之么?
当然了,魏延的计策未免还是过于大胆,小看了天下英雄。长安城中的牌坊们再拉垮,想来也不至于害怕区区几千的先头部队;但现在——现在,迫近长安的可是诸葛亮率领的蜀军主力,这压力可就完全不同了。
连司马仲达一流的人物都去而不返,眼见是被西川轻松料理了,你说大家又能拿诸葛亮怎么办呢?
所以,郭淮的口信送入长安,立刻就激起了意料不到的反应。长安上层立即封锁了消息,在聚头几次对齐了颗粒度之后,开始迅速采取行动——喔,并不是什么加强战备,巩固城防,而是以向洛阳京师通报消息为名,将金银细软统统打包,让家小血亲混进了商队,出城后一路狂奔,直扑——直扑青州而去。
——诸葛亮要“兴复汉室,还于旧都”,西汉的旧都在长安,东汉的旧都在洛阳;你说诸葛亮打下了长安,下一个会去哪里?诸葛亮要是打下了长安,东吴八成又要跑去打合肥;西面和南面战火纷飞,不也只有靠着大海的青州,还能稍微安静一点了吗?
送走家小之后,长安的高层才收拾心情,下令关闭城门,坚壁清野,预备长期坚守。长安毕竟是前朝的古都,城墙高耸,城池坚固,就算一动不动当王八,也总可以和蜀军长久耗下去。局势走到现在,要想反击蜀军,一举取胜,当然是没有什么可能了,但坚守得稍微久一点,以此作为拉扯的筹码,那还是很有可能的嘛!
所以,长安留守的老宝贝强硬拒绝了蜀军的使者,表示“忝在职守,不敢有违”。不过,在拒绝之后,他们又话锋一转,拜托使者向诸葛丞相带去殷切的问候——就算两国相争,彼此也要体面嘛!
可惜,诸葛氏的反应却叫老宝贝们大大的失望了。数日之后,蜀军的使者去而复返,却没有就先前的善意做出任何回应。相反,他的回答愈发斩钉截铁,真是叫人齿冷:
“尊驾是说,西蜀仍旧不肯承认九品官人法的划分?”
“是的。”
老宝贝们的脸色终于完全变了。
第112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