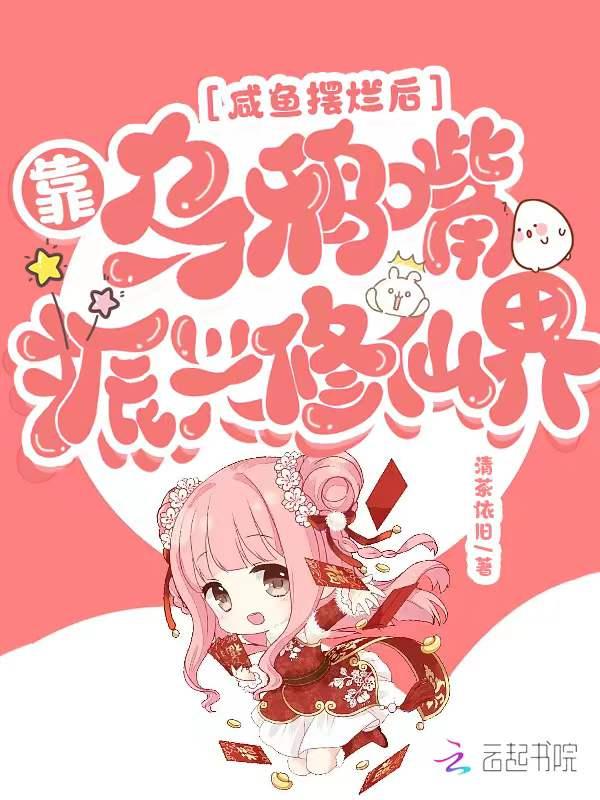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浊尘寻欢录 > 第31章 生死容易低头难(第2页)
第31章 生死容易低头难(第2页)
宁尘心里也清楚着,只是嘴上仍不饶人:“嗨呦,这也亏得我戳了两下,您才把事儿办了。我以后要是给干成植物人儿了,还有人能替我戳两下吗?”
尹惊仇再忍不住火气:“我操你妈!老子这才当了一天的监国,前些日子我说了算吗!?”
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宁尘不好再挤兑人家,哼了一声不言语了。
尹惊仇搁那儿气鼓鼓瞪眼,贝至信只好哈哈一笑打个圆场:“事难躬亲,殿下监国之后更是琐事繁多,还需多多拢纳贤臣,才能滴水不漏。”
虽然是就坡下驴的废话,尹惊仇倒也光棍,直切正题:“游子川,明日本宫要与三部太仆会面议事,你随我同去,行不行得?”
宁尘咧嘴:“您这说的什么话呀,您一国之主,哪用得着问咱这做臣下的行不行啊。”
他阴阳怪气,尹惊仇暗咬后槽牙且不计较,只转向贝至信道:“贝先生,明日我作何安排。”
“仙王竭力一吼,已为殿下开了太平路。三部忌惮仙王之威,自然降心俯首,观望者不会再留二心。但若是某部与尚荣提前勾结,便会知晓仙王如今已不堪一战,左右是吓不住。明日最关键,就看尚荣是否现身与会。”
尹惊仇:“此话怎讲?”
“尚荣要是心中没底,殿下召见三部太仆,他定然会到场观瞧局势、作些风浪,好叫三部心生忌惮,不敢全心侍奉殿下。可如果早已有某部归心,他有恃无恐,自会托词避见。”
贝至信转向宁尘:“子川,你明日不要显露锋戎,回话时若能像今日这般插几句不知轻重的,倒是可以掩人耳目。大蚀国势力之间的分寸你不熟,还是先摸清黑甲军中是否藏有元婴,以定后计。”
听见贝至信话里话外挑自己理儿,宁尘老脸有些害臊。待谈完事,两人一同离堂之时,宁尘忍不住拽着贝至信发起了牢骚。
“老贝,你这胳膊肘有点向外拐了啊。”
贝至信微微一笑:“殿下性中带火,你又何必犯他不悦。后面还需依托他办事,现在逞了口舌之快,将来不免后悔。”
宁尘咂么咂么嘴:“先前尹惊仇卧薪尝胆,极有城府。怎地这次回来,他却一副咄咄逼人的模样了。”
贝至信衡量一二,终是开口道:“只是对你那样罢了。”
“什么意思?”
“殿下逢举大事,敌我内外、轻重缓急,无不拿捏透彻。唯独对你有失分寸。”
宁尘哼气儿:“我不惯着他呗。”
贝至信摇摇头:“殿下非常想要你。”
宁尘浑身起了八斤的鸡皮疙瘩,压低声音:“他还好那一口儿呢?”
“想哪里去了。尹惊仇宏图在胸,百废待兴,手底正缺有勇有谋的贤臣良将。他这辈子,有过君臣父子,却没有过朋友,更不知怎么以朋友身份待人。别人的冒犯他可以巍然不动,对你却有心无力。你的性子恰对他的胃口,又偏偏难以驯服。你一作怪,他自然烦躁非常。”
宁尘哈哈一笑,随口道:“我逍遥惯了,总闷在一处可要憋死的,他非要我听他话,怕是要坏了现在的情分,我多哄着他就是了。”
这是在太子府内,虽然屏蔽了外面的窥探,却保不准太子亦有耳目在此。
贝至信这话不仅是说给自己听,也是说给尹惊仇听。
当局者迷,贝至信解明尹惊仇心思,或许也是为了点破他尚未自知的蠢蠢欲动。
宁尘对尹惊仇没有什么成见。
人非圣贤,自己处在那个位置未必能做的那么周全。
贝至信最初为二人搭线,宁尘便暗赞尹惊仇是个人物,换作旁时,与他喝上一口子,称个兄道个弟也未尝不可。
可是人家眼中只有仙王宝座,想的是拿自己当狗使唤。
肩旁齐,为弟兄,一个非要骑在另一个脖子上,那就没什么情谊好讲了。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事情了了,一拍两散伙便是。
只是在这之前,也该提防提防尹惊仇了。
***********
往日的王宫内院,不说是熙熙攘攘,至少也是各色侍女仆役人来人往,少不了热闹。可如今各阶嫔妃宫门深避,再无平时的串客游园。
下人们更是如履薄冰,生怕出什么差池惹祸上身。
熟悉的狂虎部侍卫调换一空,只有新晋的黑甲军分两班轮值守备,偌大内宫就靠这点人巡逻站班儿,一时间竟显得空空荡荡、杳无人迹。
一班六十人,偏生在内宫东翼的暖玉阁外,如今竟凑了七十多个。
“操,你们仨不是巡逻吗!怎么又过来了!”一个靠在暖玉阁回廊下面的黑甲军骂道。
“怎么的?还不许人尿泡尿了?”三名著甲当班的金丹并行一列,顺在骂人那位后头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