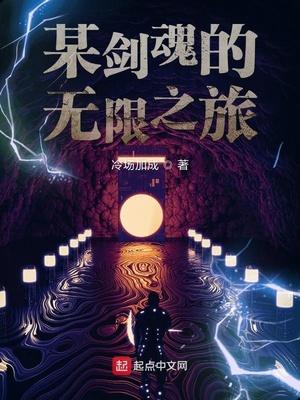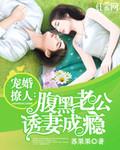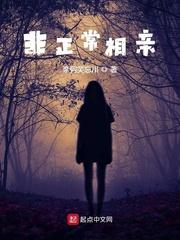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都重生了谁考公务员啊 > 第653章 天上宫阙下(第2页)
第653章 天上宫阙下(第2页)
当晚,团队举行闭门会议。议题只有一个:如何将“火种模式”规模化复制,而不失其温度与深度。
“我们必须建立区域协作网络。”林晚晴提出建议,“在各省会城市设立‘火种驿站’,招募本地大学生、退休教师、社工组成导师团,形成属地化支持力量。总部提供标准化课程包、督导机制和技术平台。”
“还要防止‘精英化’倾向。”小赵补充,“不能只挑成绩好、表达强的孩子。那些更沉默、更边缘的,才最需要我们。”
江辰点头:“增设‘静默守护者’机制??针对极度内向或遭受创伤的学生,采用非语言互动方式建立信任,比如绘画日记、音乐疗愈、植物养护等。”
决议通过后,系统立即升级。新版本增加了“成长节奏识别算法”,能够根据每个孩子的行为模式调整干预频率与形式。有的孩子适合每日打卡鼓励,有的则需要长时间静默陪伴才能敞开心扉。
七月十五日,阿依古丽第二次传来作业。这次是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看见的第一片海》。
>“老师,我没见过海。但我梦见了。蓝色的,很大很大,比沙漠还宽。浪花像羊群奔跑,月亮落在水面上,像奶奶摇的银勺子。你说深圳靠海,那我希望有一天,我也能站在海边,给你读这篇作文。
>
>现在我每天教弟弟妹妹读书,用你们给的平板。村里有人说我是‘汉话婆’,可我不怕。星星不管在哪片天空,都是亮的。”
江辰打印出来,贴在营地那十棵树的照片旁边。第二天,他亲自带队,第三次奔赴南疆。
这一次,他们不仅带去了新的教学设备,还有十台小型海水淡化原型机??那是江辰托朋友从中科院借来的实验样品。他对孩子们说:“既然你们没见过海,我们就把‘海’变成能喝的水。”
当清澈的水流从机器末端汩汩流出时,全场寂静。片刻后,爆发出欢呼。
阿依古丽捧着一杯水,认真地说:“老师,这是我喝过最甜的水。”
秋风吹起黄沙,也吹动了更多希望。九月开学季,“萤火课堂”注册用户突破十万。来自北京、上海、杭州的上百名在职教师自愿报名成为线上导师,每人每周义务授课两小时。一些重点中学甚至开设了“反向支教”项目??让学生们录制微课,送给远方同龄人。
更有意思的变化发生在城市另一端。一批曾被视为“问题少年”的职校生,在听完陈默的分享后组建了“蓝领创客社”,利用废旧零件制作简易机器人,参加市级青少年创新大赛并获得三等奖。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不是被淘汰的人,我们是还没发光的火种。”
江辰去参观展览时,一个戴着黑框眼镜的男孩拉住他:“江老师,我能加入你们吗?我不想一辈子修车,我想造车。”
“你已经在路上了。”江辰拍拍他的肩。
冬天再次降临,但这一次,寒冷没能冻结热情。国家教育部正式发文,将“青少年发展风险智能预警系统”纳入基础教育现代化建设指南,要求各地因地制宜推广。财政部拨付专项资金,用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流动儿童服务体系建设。
而在民间,“破壁计划”已成为一种精神象征。社交媒体上兴起#我是萤火#话题,数万人分享自己被照亮或试图照亮他人的故事。有人上传视频:深夜便利店,店员悄悄为写作业的环卫工子女打开暖光灯;有人讲述经历:大学室友得知他来自贫困县,默默帮他申请助学金却不留名。
江辰收到一条私信,来自当年那位签了《数据授权终止书》又悄悄回心转意的母亲。她说:“我现在是社区志愿者了,专门帮其他妈妈理解政策。原来我不是无力,我只是从前没人告诉我怎么用力。”
泪水滑落屏幕。
除夕夜,晨光实验室举办线上团圆会。全国各地的“火种”学员、志愿者、合作机构代表齐聚云端。背景音乐是孩子们合唱的《夜空中最亮的星》。
江辰致辞时没有讲宏大愿景,只念了一段摘录自系统日志的话:
>“2025年4月3日凌晨两点十七分,云南怒江傈僳族女孩李娜妞完成首次在线答题。耗时四十三分钟,错七题,重做三次。提交后留言:‘我想看看答案。’
>同日18:05,系统推送个性化解析视频。
>4月5日19:12,该用户再次登录,正确率提升至82%。
>4月12日,她给导师发消息:‘老师,我觉得我可以考上高中。’”
“这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江辰停顿片刻,“不是改变世界,是陪着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走过他们生命中最暗的一段路。”
零点钟声敲响时,林晚晴发来一条消息:“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你说你不信奇迹。现在呢?”
他回:“我现在不信奇迹,我信坚持。”
新年的第一天,阳光洒满渔排。控制系统自动推送当日简报:
【当前在线守护儿童总数:142,806】
【今日新增希望记录:613条】
【桥梁承重能力持续增强,结构稳定,运行正常。】
江辰站在教学舱外,看着海天相接处升起的朝阳。风依旧咸涩,却不再冰冷。
他知道,这条路没有终点。只要还有孩子在黑暗中摸索,就会有人点亮灯火;只要还有灵魂渴望生长,就会有人默默递上土壤与雨水。
而他们,将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