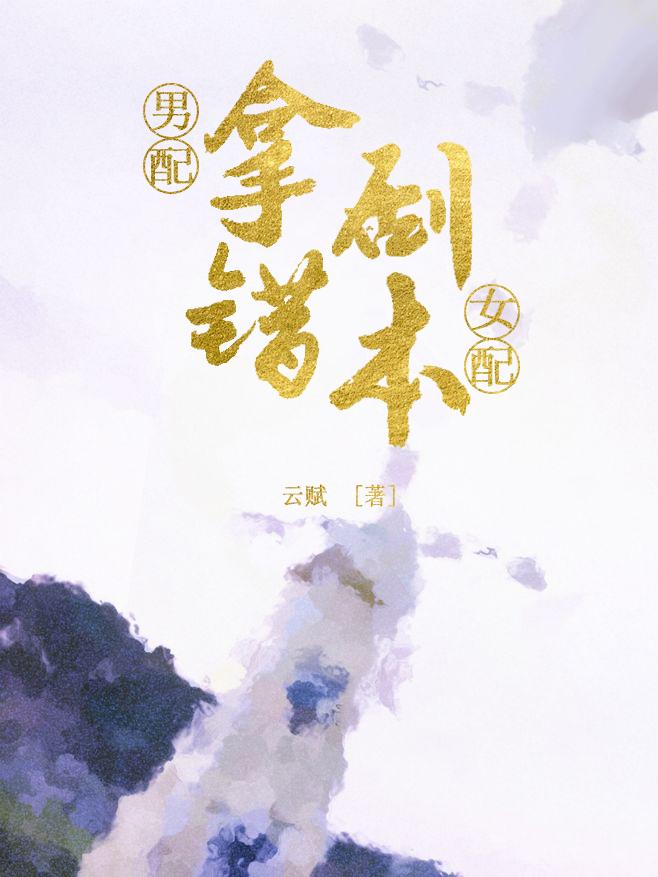零点小说网>全能大画家 > 第九百八十章 在教室里(第3页)
第九百八十章 在教室里(第3页)
看上喜欢的,无论贵贱,都让曹轩随便挑上。
“三件,不,五件。”
曹轩也大笑,然后说好。
真的是好画。
真的是珍藏。
也真的是雅士。
两个人就这些画对谈到深夜,官员这才派了司机送曹轩回去。
“我知道那位先生说的是真心话。”
“那些画也真的都是好画,我记得有八大山人的,有唐寅的,有董其昌的字……换个场合,换个地方,谈论这些事情本身是一件值得快慰的雅事。”
曹轩说道,“那天晚上我们说了很多很多,可我总是忍不住想起,在儿时所看到的僧人在油灯下刻木版,我问他一幅画能卖多少钱时的样子。”
“他的牙齿映在油灯下的模样,就清晰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位官员让姨太太给我敬茶,大笑时的样子,也在我面前。”
“那刻我的感觉不是愤怒,不是荒谬,而是清晰意识到了……我真的在目睹着历史。我整个人生中,唯一一次,有那么真切清晰地感觉。”
曹轩说。
“我无比明白地知道,不管老蒋有多少个师,有没有美援,不管他在报纸上怎么说的,怎么宣传的,不管他能杀多少人,不管战争一旦爆发,走向是怎么样的,初期是顺利还是艰难,我都知道,最终会赢的一定是我党。”
“这就是历史无法抵挡的浪潮。”
第二天。
曹轩把家当收拾好,随便收拾好了行囊,带了这些年收集好的版画,买了一张当天最早的船票,便由沪上坐船去了津门,然后直接便去了陕北。
“顾为经,你告诉我,这算不算是对我人生影响最大的一位画家?”
老先生问道。
顾为经点点头。
“那那位僧人呢?他见到你怎么说。”
“死了。”
曹轩说道。
“他组织武装部队和群众反击日本人的扫荡,在40年代初便牺牲了。战争期间,千千万万人都在死去。”
老人的语气很平静。
听不出明显的情绪起伏。
良久。
他才又说道。
“我一直都很很后悔,小时候的顽皮。”
“毕加索是一位伟大的画家,他也一样。他们全都是人类艺术史的一部分,尽管两个人的受人关注完全不同,对我而言,他也许比毕加索,在脑海里印象更深。”
顾为经沉默了。
![每个剧本都要亲一下[快穿]](/img/36216.jpg)